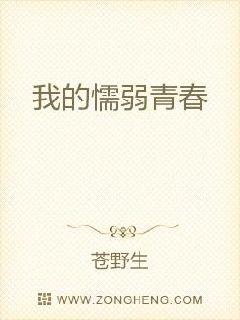我已经不记得那天的我,是如何走出教室门的了。关于这个,我的记忆一片空白。我只记得海伦老师抱着她的课本,像一阵轻风般,低头从我的目光中低头走过。我就被那轻风带到了门外,我看着她的倩影慢慢的变小,消失。我还好久没缓过神来。
洱海的天空,充斥着乌云。我立在人来人往的教学楼前,望着乌云,无法拔步离去。洱海碧蓝碧蓝的,横卧在山下古城的那边,登上点苍山,我们可以看见洱海的整个轮廓,但是由于学校只在山脚,所以,她只是横着的一片水,像一叶舟。点苍山头的白云垒成一座座尖尖的山峰,从碧绿的山头一座一座的连接着,向地面而来,从延伸到人间的山的巨大的触角上滑下,那山的触角深入到村庄之间,白云化成的山峰也就低低的浮在村庄密密麻麻的房子之上,接着云山继续往洱海上铺陈,它们横过苍山与洱海间的平地,在洱海上聚集,洱海上空原本就充斥着的云海,被三五成群,十余二十相逐的云山冲击,云海被迫分裂,人们可以看见云海底面在被云山分流后,有的云流从云山之间淌过,有的在云山之后合流,而有的则就此分开,各去各方了。数十排的云山低浮在湖面上,其上又铺开一层,其上又铺一层,金色的闪电,像黄金藤一样在云山间闪现,也有时掉下湖面去,落在湖中的两个小岛间,然后消失。雷声隆隆,而并不是什么地方都下雨,湖面上有阳光从云上直贯而下,捅穿云层,到达湖面,有时是一道两道,有如巨大的黄金柱子,光落在湖面上,形成一个数道光柱合成的光台,好似天仙要降临一般。她会踏波而来,笑语盈盈。有时云层肚腹中如被射了数千数百的黄金长矛,好似雷声滚动,好似当年二十万唐军过泸水来远战南诏,而南诏在吐蕃的相助下正勇敢应战,厮杀声四起。我对《伊利亚特》的兴趣,就是这种巨大的云景所引发的,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的争吵,阿开亚人和特洛伊的英雄们的格斗,从我的口中读来,送往天空而去,那低低的云,慢慢的拂过你的头顶,带起的风和放下的阳光,让你感觉雅典娜女神从你的身后抓住你的头发说完启示离开之后,牛眼睛的赫拉又降临你的身前,而战场就在云中,近在咫尺,迈步就能踏上你反抗诸神给你规定的命运。细雨蒙蒙,也从教学楼上经过,三道彩虹从洱海经天而来,落在教学楼前,有两道被云山遮住一段,只有一道从头到尾都清清楚楚。我总是幻想,从此路上去,必定能找到我想要找到的东西。走上云端,我看见阿开亚人的英雄们正在波浪翻滚的大海边激辩,受阿波罗保护的克鲁塞斯在为赎回自己的女儿发出撕心裂肺的祈求,有着强大权力的阿伽门农在恶毒的挥洒他的淫威,而捷足的阿基琉斯在反抗着人间的不公,我不知道自己是谁,但是我要在众人都被俄林波斯山上的诸神左右命运时,站在阿基里斯的身畔呼喊,英雄们,去他的神吧,与其听那在你身后暗中劝说你的神的话,不如听你心中自己的话。古人幻想出的那些神奇的动物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风,掀着你的衣襟,你再随着那衣襟奔跑起来,诗句“驷玉虬以乘鹥兮,溘埃风余上征”就在脑海里神奇的冒出来,虽然那是破旧的衣襟,但是引来的龙与凤,却足够让人神游太虚,纵横古今。天游之乐,唯其人可得之。
一片白云从教学楼的楼顶飞过,把细雨过后的阳光给遮住了,而且这云五彩斑斓。它轻轻的飘去,为我看见平平的云底,掉下来一道云,向地面挂来,在我的头顶划过又消失在风里。
“美人如花隔云端。”
我大声呼喊,抱着楚辞就追着它跑,从那群在教学楼前对着三道彩虹指指点点的男男女女中间过去,从停着密密麻麻的小车的停车场边过去,从花草成堆,绿树成荫,小亭隐约的花园过去。可能我觉得虽然美人隔着云,我可以去靠近她吧。海伦老师不是正在呼唤吗?
一片云过去了,另一片云又过来,我低头看着书,余光里地面的云影在显示云来云往,它们从树梢上过去,我跳起来呼喊它们,我舞动着在拉丁舞选修课上学来的步伐,慢慢的我感觉不是云来云往,而是阳光去了,它又来了。冷热非常明显的体现在身上。我不知道,海伦老师的心中此刻是否也有一个人在狂舞。应该有,毕竟她也是一个女子,还是一个感情那么细腻的女子。她那些日子,在讲台上舞着裙子左右摆动的情形,出现在我的脑海里,挥也挥不去,而且我也不愿挥去。
数日里,我就在这样的疯狂之中,衣衫褴褛的朗诵着楚辞,从校园的这端舞到那一端。洱海,苍山,古城都飘动起来,南部的学生宿舍楼和餐厅楼,北部的教师宿舍区,艺术学院,理学楼,每一个花园,每一个停车场,每一个人工湖,每一个篮球场,每一片足球场,每一个体育馆,每一间教室,每一个人都在飞扬。
只是,我想到家中母亲的禹步蹒跚时,巨大的悲痛又冲进我的心里。《招魂》与《天问》的句子在口中所释放的愤怒也不能带走这种痛苦。我注定是痛苦世界里的主人。该如何,我的那种感觉到幸福的心才不会愧疚,像海伦老师给我带来快乐一样,我去带给他人快乐,正义,公平。愿我有这种能力吧。但是,我最终却成了这种愿望的反面。那种恶毒,人的恶毒啊,在我的懦弱中,它得逞了。这是一种能让我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懦弱。 那时,我才知道一个事情,人总有死,这是很清楚的,但是除了生理上的死去,自然规律中的死,人还有另外的死。文字写到这里,我不想往下继续,我真希望此刻就去死亡,我记叙着海伦老师,然后写出当日云下沉默时对母亲的思念,再想想我以后的行为,愧疚像刀一样在我的心上割,我恨不能,停下手,去到厨房拿出刀来在脖子上一抹。人世间,如何会有这样的痛苦啊,命运给你的灾祸,你可以自己抵抗,但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灾祸,你如何面对?
我在云里放荡了数日。我终于被大学追求女生的风气和海伦老师的挑弄,继续着那种放荡。我可以去向海伦老师借书,我想我们的接触,应该从书开始。我们找到共同的话题,去找到各自的思想。那么,或许我有那样的幸运,在人间完成一件美事。但是,我不知道,人的思想是有如此巨大差异的。我是那么自负而飘渺,而海伦老师毕竟年长数岁,她虽也在书本的哄骗下,掉进了梦中,但是很快她就苏醒了。
“老师,我想跟你借本书看看。”
一次下课后,我走到讲桌前,看着正在收拾课本的海伦老师,向她说道。她低着头,然后望着我。害羞里,透露出对我的这个举动的急切和矜持,这样的笑,如此的动人。她是一个比我高的女子,她站在讲台上就更高了,我只能仰望着她。我只感觉那温柔如同春江缓缓流来,有花香,有月明,如唐诗一般华丽。这笑带来的温柔,如同天赐给我一身锦衣。我感觉到身边的空气那么暖烘烘的,像只要动弹就碰到了春枝,我生怕弄坏那娇嫩的细芽。
“好的,我明天给你带来。”她又像梦一样去了。我站在烟云里,看着她离去。
我不知道,海伦老师会借给我一本什么书。我也不知道借书之后,我该如何继续。我在极度兴奋中忐忑不安。
第二天上课,海伦老师来了,我特意坐在教室的最后。她走到我的身边,递给我一本书,我拿着书一看,上面赫然写着:带上本书去巴黎。我看着这本书的题目,一阵苦笑。这群老师啊,我愿意学习一些导世扶俗的知识,她却只想着浪漫。巴黎,不就是人说的浪漫之都吗?这是我当时对海伦老师的鄙夷和成见。要是当时我对这本书的作者有所了解,对里面的内容有所了解,我会知道这不是市面上的那些口水书籍。而我将不会把海伦老师看得那么浅薄的。但是我的骄傲,让我决定,不必翻开这本书。但是,其实这个误会在这个爱情游戏里,本来就无足轻重。这注定就是个梦,梦就会醒,所以里面的一切都是虚幻。
“老师,什么时候还给您?”下课后,我问海伦老师。
“随你什么时候!”
我拿着书回去了宿舍,男生们在看成ren电影。我把书包裹在衣服里,生怕海伦老师的书和这些东西有个照面。但是,随后,我把书放在抽屉的最里面,锁上了。我不会去看这种书的,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世俗的东西上,我认为非常无聊。我想,我应该把我写作的文言散文给老师看看。这样她就能知道我的心了。海伦老师的梦,是希望尽早走入安稳的婚姻,以保障她的生活和她的学术研究,而我则想着,如何到最底层去有所作为。所以,这个洱海边的梦,虽对我与她的感情是件荒诞的事情,但是对于我来说,可以让我更明晰自己的思想。至于海伦老师的思想,我当然也能看明白,而在她呢,她当然更清楚。所以,这个梦,在她而言,是件画蛇添足的事情,她已明白自己所要走的道路,走就是了。至于去了解我,了解和她不一样的世界,我看也没有必要,她与她的那一群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愿,了解和自己不一样的世界,在他们而言是一件困难而不屑的事情。这是我所鄙夷的思想。海伦老师所设置的课前演讲,是一个大的进步,比起其他老师高高在上,不愿纠缠,更亲切些,但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而已。
我不会去看这种愚蠢的书的,和看那恶心的成ren电影比起来,这样的书更加恶心。直到后来,我在哀牢山里,非常寂寞时,再次去查这本书的来历和内容时,我才后悔,自己当年只是把字面意思理解了,而在这后悔之前,我还干了一件禽兽不如的事情。生活的艰难和痛苦能让你变的如此可怕,我自己看着都不敢相信,原来我如此恐怖。
但是,大学时,我不知道。我把她的书放在抽屉里最里面,自己还是看自己的楚辞,史记,想到的还是我自己家的贫穷,我去过的同学家乡的贫穷。海伦老师如此娇滴滴的,还能读博士,不用考虑经济问题,一定是在一个小康之家或者更加富裕的家里长大的,我的衣着,一身破棉袄,她会不嫌弃,而且能示爱,并不是她看得透贫富,能够看见表面之下的珍贵,而是她被她上过的学,读过的书欺骗了,她自以为自己是这样的女子,又或者,她果真是这样的女子,但是她并不希望自己去接近这样的珍贵。我所谓的珍贵,或者在人心中并不是珍贵,人们只有能自己把握的住的实际利益,他们才说是珍贵,对他人的同情和帮助,对祖国,民族的关心和热爱,在他们那里是虚伪的,甚至是可以用来作为幌子去骗取利益的。但是,那些贫穷和艰苦,却真真实实的在那里,那些灾难和恶行,也真真实实的在那里。我不知道,是谁给我的这些思想,父亲?母亲?或许,我把他们比较小的这种愚蠢放大了吧。
我在大二的寒假,和一个苗族的男同学去了他家,他家在楚雄州中村。我们坐汽车到楚雄,又坐班车到中村镇,又坐拖拉机到他家的那个大山,又走了几个小时路。经过两天,在晚上到了他家。我基本没有看清他家的人和他家的房子,吃了饭,就累得睡觉了,梦里,还在走白天走过的那根独木桥。一条湍急的河水上高高的架着一根木头,离水面三四米高,两岸隔四五米远,在岸上看着,好像没有什么,一走上去,脚下跟什么也没有一样,身体不能大动,眼里上面是天,下面是水,像被突然扔在了宇宙之外,战战兢兢过去了,好久都后怕。
“牯里,你睡着,我去砍柴去了。”同学一大早就起来,他和家人就去山上砍柴了,牯里是苗语兄弟的意思。我一骨碌爬起来,大声说:
“我也去,我也去。”
“没事,你多睡一会儿,等一下我回来给你煮饭吃。”
我听到这里,羞死了,做客做到当公子哥的份上了,我来干什么。
“我来的时候不是就说了吗,你们怎么样,我就怎么样。”
“那好,你洗好脸,出来,我等你!”
我洗好脸,出来,准备吃饭。但是外面却喊走。我走出去,只见牯里已经换下在学校的西装皮鞋,穿上了破衣服和绿色的解放军鞋,背上背着竹篓,里面全是锅碗瓢盆,手里提着一把长长的柴刀,站在地坪中央,正侧身望着我。地坪边沿一排小树,而外面是一片大山,遥远的大山。我非常兴奋,两天后才恢复正常人的感觉。
“吃早饭吗?”
“去山里面吃,你看我带着锅碗瓢盆,而且我们山里面只吃两顿,不像学校和你们湖南。”
“不会饿吗?”我和牯里一边走一边说,只见屋后的路上有一架板车,一头骡子在前面等着。车子边,已经有一堆劈好的木柴,他们已经干了很久的活了。
牯里把背篓给我背着,让我坐着,但是车子的两边没有抓的,就一块木板。
他一声坐好,我就被颠簸了十几分钟。赶骡子有两种吆呼,一种是“驾”,“哇”,“得”这样的命令,一种是“刹德罗” 这样的叫骂,“刹德罗” 是苗族话畜牲的意思,而驾驶呢,用两个工具,一个是缰绳,一个是刹车,拉左边缰绳,骡子就往左,拉右边它就往右,你叫它停它不停,就压刹车。
车子在路边停下来,路两边都是山。我下了车,只听见有斧子在砍树的声音,我忽然想起诗经里伐木丁丁四个字来。抬头,只见天空都被树林盖住,四望,全部都是树和草,耳中传来砍树声,偶尔还有一两句清脆的鸟叫,鼻子里有泥土松树混合的气味,有时候是清香,有时候是腐臭。
就在我用五官感受这山林时,只听见,一个慢悠悠的拉曳之声,循声望去,只见树林的高处有一棵树的树冠慢慢倒了下来,它极力的拉曳的其他大树的枝叶猛的回弹回去,打在树上的声音,它蹭着其它大树树干的声音,在树林里回响,最后只听见沉闷一声响,树林里于是安静了。
“你爸爸妈妈在那边。”
“对的,这些树都是冬瓜树,容易长,容易砍,也容易干。”
“真的?等一下我也砍。”
“好的,我去打水,你去我爸爸妈妈那边。”不知什么时候,牯里一手提了一个大白酒桶,他往那堆枯黄但是任然很高的飞机草里面去了。
我在路边找了条小路,向着树到的地方走去,不久看见树林中间有一块圆圆的空地,布满了劈好的木柴,牯里的母亲,戴着一块头巾在劈柴,牯里父亲在空地外不远处正将砍倒的树去掉树枝。
牯里母亲望了我一眼,笑了一下,让我在旁边看着。我站了一会儿,树林里的寒气让我感到很冷,我就跑到牯里父亲那边要求劈柴,他哈哈大笑,教了几句怎么使用斧子,就把斧子递给了我,牯里母亲用苗话低沉的说了几句,像在骂人,牯里父亲悠悠的回了几句,可能牯里母亲怕我干不来,我第一斧子下去,果然没把树枝劈下来。他俩都笑起来。
不久,牯里提着两桶水回来了,他开始做灶。他把两块大石头先并列摆好,中间隔着一步的距离,又拿块石头堵住一端,一个临时的灶就做好了。我感到非常新鲜。
他抓了几把干叶子,用打火机点燃,放好在灶中,然后架好几根细柴,自己就去淘米了。他回来时,火已经大起来,他把几根粗木头拿进去,不久火更大了。于是他在上面煮饭热菜。或许,很多事情,只要有方向,简陋的工具也能完成的。我看看那几块石头本来就躺在大山某处,什么也没有,但是一经摆弄就是一个灶,而且能煮饭热菜,最后能补充体力,让我们继续干活。太简单直接了,我读中文系,本就是爱好文学才填的,那些文字我是能摆弄了,虽然也如这石头般粗糙,但是表达一个意思还是可以的,但是我要用这个灶,烧一锅什么样的饭菜呢,我要把它们招待谁呢。我不知道,我想起家乡那些粗略听说过的顶天立地的人。但是,曾国藩到新中国的这一批批湖南人,我当时还没有通过书籍了解过。我像其他人一样把他们学习完了,就抛在脑后了,像物理里面的核辐射,化学表一样扔到以前的世界里,所以,我不知道我该煮一锅什么样的饭菜给这个时代。
柴堆得太多了,就装上车子,满满一车。我随着牯里运柴,在碼柴时,可以帮他忙。那骡子遇着下坡,飞一般跑,遇着上坡,实在走不动了,就横在路上,任你打骂。于是我下车推,这样车子才动,这下把骡子惯坏了,它遇到小坡也横着,要我下来推。这个骡子不像它的主人一家那么实诚,倒想是城市里面的人。
电视机只能看几个台,因为他们接收信号用的是一个锅一样的接收器。而且在大山里,电视里的内容太远了,根本引不起兴趣。牯里带着我满山跑,去到姑娘家玩。这是一个很累的事情,因为晚上走山路,太困难。但是,家里又没有什么好玩的,我只好随他去。
牯里带着手电筒在前面探路,我跟着。路边的野草打在裤腿上,噼里啪啦的响。我们一路说着话,走到一个山顶,突然吓一跳。因为那满天密密麻麻的星星那么清晰,那么低,好似爬上了楼梯直起腰,头就会撞到天花板。我站在原地,啧啧赞叹这个美丽的星空时,牯里已经下到山下了,他在用手电筒照我,我于是也下去了。到了一户人家,他家的女孩不在,牯里也没有回家的意思,主人提来一瓶酒,端来一盘瓜子,两个人就在火边笑谈起来。我听也听不懂,也不会吃酒。于是自己找着路回去了。
第二天早上,牯里一身酒气躺在我旁边。我起来后,他也起来了,但是他的衣服全是泥巴,床下只有一只皮鞋。
“我昨天吃多了,回来时掉在路下边了,他奶奶的,姑娘也没看见,皮鞋掉了一只。”
我哈哈大笑起来。
于是我们白天砍柴,晚上去逛大山,或者在女孩子家唱歌,只是那些姑娘都是些和我另一个世界的人,我只能欣赏到她们身体的美丽。
有时哪一个人家结婚了,一次牯里带着我去做客,在接近主人家的山头上,看见年青的男女,从各个山头聚集,女孩子穿着她们民族的衣裳,有苗族的,彝族的,这些是在她们平常不穿的,当然穿得最多的是当代时兴的衣服,而小伙子居然带着笛子和三弦来了,他们在山道上前后呼应,男孩子在女孩子身边来回跑动搭话,就像春天在菜地里看见的蝴蝶们一样,前后相逐,上下翻腾。我看着,看着,觉得真有意思。一个小伙子赶上来了,他穿着一件彝族的坎肩,背着一个三弦,他和我牯里说着话,我要过他的三弦欣赏,因为上面有一排排红字相当的显眼,我一看,是用红墨水抄的一首唐诗,张九龄的感遇四首,但是有几个错别字。我心里暗笑,但是不可否认,那是非常真诚的追女孩子的准备。我想城市里面的男人早就没有这种古老的情趣了。
也有年青女孩赶上来了,彝族的大裙子非常美丽,黑色与红色交替着,在萧瑟的大山里格外的耀眼。她们都低眉的说话,有时害羞的偷望。牯里和其他小伙子都尽情的与女孩子们攀谈,我在旁边跟着望着。
“牯里,这里的女孩子不漂亮?你怎么不和她们说话,又不是让你娶回去,你难道不喜欢女人,不像你在大学里的样子啊。”
我只是笑一笑,我会调情,但是我还是没有逗弄她们。
婚宴就在主人家房子外举行,地坪上敞天摆了两排桌子,一排五个桌子。早来的已经入席正在吃着,我跟着牯里来到一个桌子前,看见一个老人家戴着眼镜在桌子后坐着,他正在一个本子上记着什么,原来这是挂礼的地方,旁边有人端着盘子,有瓜子花生和茶水,在地坪边沿四方都是人,在房子走廊上也是人,我跟着牯里往主人家的房中去坐,在一个房里,对面一个大电视机,靠左一个沙发,前面是茶几,但是里面挤满了人,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,正骄傲的坐在里面,但是她有些斜斜的躺着,好似她非常满意自己的美貌,正在那里等着男孩子们的追捧,她穿着鲜红的衣服,加上她娇嫩的肌肤,真正不可思议,在大学和城市,到处有女孩子,和美丽的女孩子,但是在这里半个月很难见到女孩子,除了每周去赶街才能看到,而且那些女孩都平庸无奇,所以看见这个女孩,我的眼睛也离不开了。牯里看见我失态的样子,哈哈笑起来说:
“不错,是个漂亮的小妞。”
果然,好多小伙子围着和她搭话。坐在她旁边的女孩们都嫉妒得不行。
真有意思,真有意思!我在心里说。那炫耀,那嫉妒,那追捧,都那么直辣辣的。不像城市里面那么矫情,有那么多考虑,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。
我站在门口,痴痴的看呆了,不仅是那个红衣服的姑娘,还有其他的姑娘和小伙们在一起的这个气氛。
当那个女孩把眼睛望向门口时,我才感觉到自己的突兀。牯里把害羞的我拉去吃饭了。
我的脸红得不行,因为这是春天,那些长在屋前的桃花李花都开了,我望着它们,像吃醉了一样。我虽在吃饭,但心里也想着那个红衣女孩。
“晚上有跳脚,你也跳。”牯里说。
“看那个,那是给跳脚跳到很晚不回去的人睡的。”我顺着他说的方向看去,只见主人家房子有一个放草的仓库,没有门,里面放着许多水稻秸秆捆。
我一看那个破落样,一口饭快喷出来了。这群可爱的人啊。
“没有什么,以前他们跳个两三天都有的。”
我真喜欢他们。
但是我突然想起我的母亲来,母亲在我上大学的那个夏天,自己背着农药桶冒着中午的烈日去水稻田打农药,中风偏瘫了。我一下想起那个漂亮的红衣女孩,一下想起母亲缩着左手,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,很是惭愧。或者我不应该来这里,我应该和其他争气的人一样去深圳打一份工,给母亲添一些衣物和药物,让她高兴,但是我没有。我在这样的矛盾中徘徊了一阵,又被外在的热闹拉回去了,苍天啊,我要是知道我以后会如此对待我的母亲,我会离开这里,去一个城市端盘子也好,给母亲带去一些欢欣,这样不会让我以后如此愧疚痛苦。辛轩,你就是一个不孝的畜牲。我只有死去,才不会那么痛苦,但是就算是死去,也抵不掉我犯下的罪过。
慢慢的,天黑下来了,屋外的空地上,桌子已经搬走,中间堆起一个巨大的火堆,老人,青年小孩在空地边围成一个圈子,一个老头穿着蓑衣,提着一把像关羽拿的那种大刀在火前挥舞,一个老人拿着笛子在旁边一边跳一边吹,清脆而简单的旋律响起,大家跟着拿大刀的老人开始边跳边转。踏地声和笛声很好的相应着。火星子在火上冒着,飞到空中和天上的星星飞在一起,不知哪是星星,哪是火星。
牯里笑呵呵的走入了圈子的队列里,前面是一个胖大嫂,后面也是一个胖大嫂,我看着他们,笑个不停。换了几个步法,慢慢开始,是一种牵着手跳的步法了,这时牯里已经退下来,突然他拉着我的手走去队列里,我不会跳,使劲挣脱,但是忽然就站在一个人旁边,是那个红衣服的姑娘,夜晚里,她娇嫩的肌肤和黑漆漆的眼睛也非常显目。她看着我发呆的样子,笑起来,而队列已经转动起来,她催促着我往前走,我把脚也随便甩起来,只见牯里前面也是一个年青女孩,他们抓着手正高兴的跳着,牯里一回头一把抓住我的手,我往后一望,那个姑娘的手已经抓住了后面大嫂的手,那我还怕什么,我一把抓过去,是一只柔嫩的小手,手如柔荑,我真想把那只在我手中攥着的手拿过来仔细的看看,和这手的主人在那桃花树下独自的说话。我心里这么多想法,但是一下子就被热烈的气氛赶跑了,我一点也不能集中精力思考,我像一个中了魔一样的人跟着他们在跳脚。牯里可能跳得太高兴,他把皮鞋踢出去了。
不久,这一个步法结束了,那个桃花一样的姑娘离开了。我没有去找她,我的心里没有山里人古老的爱情的观念,我只有城市里面的矫情。
深夜,我和牯里回去了,离开时,瞥见房中那桃花一样的姑娘在一堆女孩中间应付着其他小伙子。我们离开好远好远,还能听见踏地的声音,像打雷一样。
晚上我的血液也像沸腾了一样,做了一个和姑娘云雨缠绵的梦。
牯里父亲看见我和他儿子的友谊,想起了他的老友,他一天早上指着神龛下面一个桌子说:“这是我年青时候的老友给我做的,几十年了,我要去武定走亲戚,正好到他家坐坐。”
我一听说他要走过去,于是我请求跟着他去。于是我们出发了。走到中午,在一家店里吃了碗面条,我们继续在山里走,忽然牯里的父亲说要睡觉了,牯里的父亲吃了点酒,可能醉了,他于是把包枕在头下,在路边就躺下睡着了,大卡车过去,把灰尘扬起来,飞在他身上,他也不管,我看着这大山,也不知道干啥,于是在他里面一些,找了块石头,在一个干净的枯草堆里也躺着睡着了。真是何处天地不是家啊!
也不知道睡了多久,他说走了,我就跟着他走。一路上我们没有很多话,因为全部是山路,所以我也不感到寂寞。
走到晚上的时候,终于,他指着山下一个村说,到了他老友村里了,我望去,看不见村子,这时天上星星都已经出来了,只望见一些灯光。我们走过去,就听见有狗在村口叫。这时牯里的父亲好像感冒了,有些不能走了。他领着我到了一家人家,喊了半天,也没有人答应,他推门就进去了,打开灯,这是一个木楼,他找了半天,在一个房间找到一个干瘦的老头,躺在床上,一屋子的酒气。牯里的父亲也迷迷糊糊的,他含含糊糊的叫我去找个地方睡觉,自己就在那老头床边的床上睡下了,我这下慌了,我也找不到灯,我一顿乱走,走到一个房子,却感觉脚下有很多草,我拿起来走出来在灯下看,果然是草,我回去把草放下,找了半天,把灯拉亮了,看见一头牛在槽后望着我。我吓了一跳,马上出来,后来,终于找到一个床,脱了鞋子就睡上去了。
早上,牯里的父亲和老头在火塘边做饭。牯里的父亲,感冒还没有好,缩在一堆,他看我起来了,红着眼睛望着我说:“这还是到了一半,我感冒了,不去了,吃了饭回家。”
他的老友给他熬了一锅草药,他喝了。我们吃过饭,就往回走。
回到家,牯里和他妈妈听说我俩的事情,都笑死了,但是我觉得不错的,至少达成了出发时的目的。来回的那条大路上回荡着一份友谊。
过年后,牯里的父母去走亲戚了。牯里代替他的父亲,去大山里背木头。听他说,是十几个人一起抬,那木头可能有上百年的年岁,所以又粗又重。有几天他晚上也没有回来。
一天晚上,我独自一人正在烧水,要洗脚睡觉。忽然有人进来,是牯里的堂弟,正在读六年级,他说,牯里家的骡子可能生病了。我随他到棚子里去看,用手电筒一照,只见那头蠢骡子,横躺在地上,在那里哼哼,我记得几天前,我牵着他去外面吃草。回来时,骑着它,它一把给我摔下来,背结结实实的摔在大地上,我半天捂着胸口疼得说不出话。现在,见它这样,真解气。
“生病了,肯定是。”
“你爸爸妈妈在吗,你哥家里就我一个人,我不会治病啊。”
“我哥哥会找草药。”